|
生物学哲学中的纲领方法论
我们认为,探究科学哲学通用原理在生物学理论中的特殊表现及其可使用限度,正是生物学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文主要讨论在科学哲学中享有盛名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普遍原理(就其合理成分而言),能否成为分析生物学理论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本章所选的典型案例是从孟德尔到摩尔根的遗传学实验研究。我们认为,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和摩尔根所领导的果蝇实验研究都是对生物学哲学作案例分析的极理想的思想材料。染色体遗传学的这一段科学思想史,为生物学的科学哲学原理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证据支持。
早在《科学思想的源流》(1994)一书中我们曾明确表示过,摩尔根所发现的基因的连锁与交换的定律,正是在孟德尔的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遇到“反常”之后,通过引进“辅助假说”消解反常的成功案例。这是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在生物学之中的胜利。在对摩尔根学派的果蝇实验发现史的细节作了更深刻的反思之后,现在我们进一步认为,纲领方法论对染色体基因论的分析还可以精致化,而且仍然很有启发力。
孟德尔研究纲领的硬核
遗传学由于孟德尔的研究工作才真正确立为科学。孟德尔(G.Mendel,1822~1884)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立足于豌豆杂交试验,借助于假设演绎法,提出了“遗传因子”的概念,发现了“性状分离定律”与“自由组合定律”。在孟德尔以前的植物杂交试验,同孟德尔那种精细的统计和实验方法根本无法相比。“遗传因子”对于遗传学的重要性是与道尔顿的“原子”或拉瓦锡的“元素”在化学上的地位相当的,因此孟德尔后来被誉为“植物学上的拉瓦锡”。而且还常有人将孟德尔的粒子性遗传因子理论和道尔顿的原子论与普朗克的量子论相提并论,这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孟德尔学说确实继承了原子主义的研究传统。
另一方面,孟德尔的研究方式,同时又是高度重视数学思考的毕达哥拉斯研究传统在生物学上的独特表现。因此,孟德尔的巧妙的实验设计思想后来得到统计学家费歇尔的高度赞赏。当代科学哲学学者对原子论传统与毕达哥拉斯主义传统评价甚高,认为此两者至今仍决定着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1][2][3]
可惜的是,19世纪的生物学家们,几乎没有人能理解孟德尔对遗传问题的试验方式和数学方法。孟德尔的传记作者爱蒂思(H.Iltis)回忆说,1899年他曾高兴地发现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论文,并告诉他的教授。可是教授说:“它是纯粹毕达哥拉斯式的东西;除了数学和比例之外,别无他物”。相反,科学哲学家却认为,在我们周围自然界那种富有意义的秩序中,必须从自然规律的数字核心中寻找它的根据,换句话说,毕达哥拉斯的研究模式对探索并发现科学定律将会有积极的示向作用。
孟德尔在《植物杂交试验》(1865)论文中,从试验结果引出了规律性的东西:(1)纯种植株杂交后,子一代(F1)的植株出现齐一性(如高矮豌豆杂交,全得高豌豆)。子代性状不是两个亲本的折衷融合(如高×矮→不高不矮),而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为了合理解释这种非融合遗传,孟德尔不得不采用“显性”(如高)和“隐性”(如矮)的概念及辅助假说。第一条姑且可名之非融合遗传中的“齐一法则”。
(2)如果F1代的杂种植株彼此再进行杂交,则其性状(如高矮)在下一代将会发生分离。诸遗传因子的数量是1:2:1,而植株诸性状中显性对隐性比是3:1。第二条就是现在称作“性状分离定律”的最初表述。
(3)如果把一些具有两个以上相对性状的植株进行杂交,则各个相对性状(如茎的高矮、种子的圆或皱、子叶颜色的黄或绿等等)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扰,按前述法则遗传。各对性状机会均等(即等概率)地自由组合。第三条就是现在称作“自由组合定律”的最初表述。更完整的名称是“多对基因的独立分配或自由组合定律”。
在物理学哲学研究中,通常把牛顿三大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看作牛顿纲领的核心假定或“硬核”,这对初步的方法论分析也就够用了。但当人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在此背后、在牛顿纲领的深处还有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宇宙严格按机械运动规律运行)与绝对时空观等富有特色的本体论假定,这种纯思辨的猜测才是“硬核中之硬核”。正是马赫对绝对时空的批判,才动摇了牛顿纲领的根本,并触发了爱因斯坦革命,这是有史为证的。同样道理,一般来说,可以把“分离定律”与“自由组合定律”看作孟德尔遗传学纲领的硬核或核心的假定。然而,如果我们追究到更深层,想看看孟德尔对遗传过程作出了什么样的根本性断言和思辨性的猜测。那末,通过对孟德尔原理的再分析,我们可以从他的研究纲领中提炼概括出几个更深层的本体论的预设:
(1)原子主义与遗传因子决定论。根据原子论的传统,宏观世界事物的一切可观察性质,都受微观层次上的原子间不同的相互配置与运动的间接支配。同样地,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因子论,生物个体在宏观层次上的一切可观察性状,都由微观层次上的遗传因子间不同的相互配置而间接决定。具体地说,孟德尔所研究的每一对性状是由两个遗传因子所决定的(分别来自父本与母本),而生物的每一个配子(卵子和精子)只包含每对因子中的一个。
(2)粒子性遗传观念,而非融合遗传观念。孟德尔认为,遗传不应当简单地看作一个生物个体的全貌笼统地传给下一代的过程,而应当分析为一个个性状的传递过程。“粒子性遗传观念”表明,遗传性状可以用遗传因子的基本单元来分析,遗传因子具有高度稳定性,相对的遗传因子(如豌豆的高矮)在杂交后并不融合(不是变成不高不矮),而是在分配中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4]
(3)机遇是有规则的,随机过程遵循概率统计规律。这是孟德尔从数学角度对遗传过程根本性质的一种断言,是他有关生物自然界总体图景的又一根本信念。20世纪生物统计学家韦林在1965年和1966年重新评价了孟德尔的遗传实验。他的结论是,孟德尔凭借直觉应用了根据现代的“现象随机模型”进行推论的模式,这是随机数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称之为“判断不确定性的统计学”。[5]孟德尔确信两个亲本的配子是对等的,就因为他直觉地把握了“不充分理由原则”或“等概率原则”。
以上所述种种核心假定乃至更深层的本体论预设,都属于孟德尔纲领的“硬核”的范畴。
第二节 纲领方法论的通用原理并未失效
我们已经牵涉到“研究纲领”、“硬核”(核心假定、本体论预设)、“辅助假说”等诸多方法论术语。为了保证逻辑上的精确性且便于对照起见,在这里有必要简要地重温一下科学哲学中纲领方法论的普遍原理。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拉卡托斯所首创,它倍受现代科学家的青睐。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在于: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配的整个理论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核心假说与深层的根本信念,一切纲领可以说都以它们的硬核为特征;硬核周围有一层必须经受检验压力的由众多辅助假设所组成的保护带。面对反常情况,保护带可以通过自身结构的调整变形来消解反常,用以维护硬核不受侵犯,并促进整个纲领通过内部的理论交替而不断取得发展;三是研究纲领具有两个主要的方法论规则。反面启发法规则――指示不该做的事,即不得将矛盾头指向硬核,纲领的根本信念不容放弃;正面启发法规则――指示该做的事,也就是在本体论的根本信念指引下,主动地调整保护带,提出处理可预期的反常的一系列策略的提示或程序性的指令,包括如何增加辅助假说和改进实验及分析技巧,如何积极解释和预言新事实并用实验加以检验等;四是保护带的调整可以朝两个不同方向进行,从而研究纲领就有进步与退化之分。一个纲领如果能产生更多可能得到确证的新预言,并能产生更有启发力的新理论,那末它就是进步的,反之则是退化的。[6]
还有必要再对研究纲领的硬核的非常特殊的哲学性质作一番解释。硬核首先表现为核心假说,通常总是由这样一组陈述所组成,它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进一层说,核心假说背后往往包含一种思辨性的猜测,一种未经检验的总体的世界图景。深层的硬核就其本性而言,它只是“形而上”的假定、是无形象的抽象本质和规律,而不是直接面对形而下的、有形象的具体事物的,因此靠经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性的。请注意,在科学方法论学者那里,“形而上学”这个词是指探讨终级实在的抽象本性和第一原理的学问,完全没有“反辩证法”的意思。
其实,纲领方法论的普遍原理对于孟德尔的遗传学纲领并不例外。孟德尔纲领也以其硬核为特征。如果否定了“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也就取消了整个孟德尔学说。就硬核的深层而言,粒子性遗传(即非融合遗传)观念、遗传因子决定论、随机数学的规律性等三个本体论预设,本身又是一种抽象理念,不是独立可检验的。只当它们与辅助假说相结合,吸收了具体的经验内容,才能转化为可直接检验的论断。
科学哲学认为,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与硬核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正面启发法作为策略性的示向原则能提供一系列的建议或暗示来充实研究纲领,为的是使纲领能对所研究现象作出合理说明和预言。例如在物理学哲学中,古希腊的原子论纲领的硬核只是一种关于宇宙本体的纯思辨的抽象的形而上猜想。自然界在宏观层次上的一切性质,被认为都可还原为微观层次上原子的运动、组合与分解。然而,由于笛卡尔在其方法论著作中引进了诸如广义的惯性原理、宇宙的运动量守恒原理和粒子相互作用原理等辅助假设的保护带,才真正使原子论纲领逐步生长成羽毛丰满的、在科学上富有启发力的研究纲领。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注意到的,在笛卡尔之后,大多数科学家都掌握了一种思考的启发式程序,即认为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定律都必须具体阐明微观粒子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7]原子论纲领的硬核的强大启发力,从道尔顿的化学原子论一直延续到现代粒子物理学,影响极其深远。
对于孟德尔的遗传学纲领也是这样。作为孟德尔纲领硬核底层的本体论预设成了孟德尔研究过程积极的启发力的源泉。正是孟德尔所持有的随机过程规则性、粒子性遗传观念及遗传因子决定论等根本信念,推动着他的有目的的实验研究,决定着他的特有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决定着他的独特的实验设计。除了敏锐的观察力与非凡的推理能力的结合之外,他的成功还在于精心选择了他的实验材料。豌豆特别适合于孟德尔的研究目的,最能显示粒子性遗传因子随机组合的宏观结果,因为豌豆是有稳定品种的自花授粉植物,容易栽培、分离和杂交,而且杂种是可育的。孟德尔又把研究工作限定于彼此间差别十分明显的单个性状的遗传过程,从而简化了实验条件。
N.玛格纳在《生命科学史》中,对孟德尔思路进行了再分析和逻辑重构。玛格纳是这样说的:[8]
孟德尔很可能最先曾经假设过:人们确实可以十分简便地预期两种雌的性细胞同两种雄的性细胞随机组合而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子代数目。这就意味着在性细胞形成时,决定特有性状的因子的互相分离的。因此,一个杂交种──“Aa” ──具有“A”性状因子和“a”性状因子的杂交种将产生只具有A因子或a因子的性细胞。在这里细胞不同的组合中,将产生一个纯A型,两个Aa型杂种和一个纯a型。这里因为A对a为显性,可以观察到的类型比例则是3:1。孟德尔的实验并没有停留在F2代上,某些实验继续了五代或六代。在所有世代中,杂交种都产生3与1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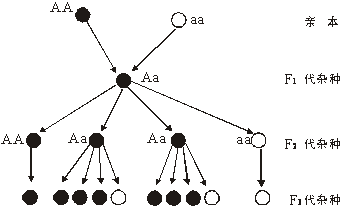
图:孟德尔表示3与1之比的杂交试验图解。
图解表示两个具有不同特殊性状豌豆株系的杂交结果。在AA或Aa基因型的个体中都表现出显性性状(=),隐性性状只在具有aa基因型的个体中(¢)才表现出来。
这里,雌雄两种性细胞及其随机结合,对子代的性状与类型具有决定性,可说是根本的出发点。显性/隐性概念或显性假说,只是说明非融合遗传现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辅助假说。显性是在杂种的子一代中所显现的性状,反之隐性则是子一代中未显现的相对性状。“非融合遗传”观念这一硬核,自然而然地能激发出帮助理解杂种的子一代的“性状齐一性”现象(如所有植株全为高豌豆)的策略性提示,所以说,显性/隐性假说的提出,正是“非融合性”这一硬核的启发力展现的结果。这就是科学哲学中所谓硬核与正面启发法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本意。同样道理,以孟德尔的“分离”与“组合”这两个遗传定律为核心的特殊理论,作为“随机数学规律”与“粒子遗传因子”等本体论信念的启发力所产生的效果而建构起来的。
正是这样,正面启发法能引导研究纲领内部特殊理论的产生,每一特殊理论并不仅围绕硬核深层思辨性的本体论假定来建构,而且也可以进入硬核内部来建构。换句话说,处在研究纲领底层的有特色的本体论假定,能不断激发出理解新事态的策略性提示,具体影响纲领内部的理论建构。
第三节 基因:从思辨工具到物质实在
一、工具主义与实在论之争
在孟德尔时代,“遗传因子”当初只是纯粹思辨的猜想,或是一种决定杂种性状及性状间关系的抽象符号,它并不直接包含物质实在性。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被三位遗传学家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之后,到1906年遗传学才有了自己的名字,1908年遗传因子也被正式定名为“基因”。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中来了:基因究竟是否具有物理实在性?如果孟德尔学说只是一种工具主义假设,那末基因只是一个的符号、方便的解释手段而已。如果说这一学说具有物理上的真实性,那末基因就像原子一样实在,具有可检验性。这就是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工具主义之争,在生物学哲学中的表现。由于细胞学研究的进展,终于找到了孟德尔学说的物质基础。
20世纪初,一些生物学家已认识到染色体行为与遗传因子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平行关系”)。尤其是萨顿的研究,为遗传学与细胞学的结合进而创立染色体遗传学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接着摩尔根于1908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果蝇实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促进了基因理论与染色体理论的完美结合,同时也为他自己确立了染色体遗传学奠基者的历史地位。
二、萨顿的对应性假设
1903年美国遗传学家萨顿(W. S. Sutton, 1877~1916)在《遗传中的染色体》一文中,提出了遗传因子与染色体一一对应的假说,清楚地说明了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具体定位于染色体上的概念。他的根据是染色体和遗传因子在细胞中存在平行现象:遗传因子在体细胞中成双,而在配子中成单,配子结合成合子时又恢复成双。另一方面,细胞在有丝分裂、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的行为也是这样。从科学哲学观点看,萨顿假说是维护孟德尔纲领的“粒子遗传”硬核的一个重要的辅助假说,属于孟德尔纲领的理论保护带的范畴。对萨顿假说而言,却存在一个明显的反常情况,这就是:遗传因子数目显然要比染色体的条数多得多。因此,即使遗传因子与染色体之间确实存在对应关系(即核心思想不变),“一对一”的辅助说法却是过分简单化了,不同的因子并非总是座落在不同染色体上。
与此相关联,孟德尔的自由组合(即独立分配)定律也遇到了反常情况。实际上,孟德尔定律在它刚开始提出的时候,就处在反常情况的包围之中。这跟牛顿的引力定律刚提出时,“被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没有两样。孟德尔本人除了豌豆外,还研究过其它许多植物。他在研究矮豌豆与红花菜豆的杂交时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只在花色遗传上是成功的),而在山柳菊的杂交实验中则根本观察不到所预期的分离现象[9](这很可能就是他同时代著名植物学家耐格里拒绝接受孟德尔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05年,贝特森(W. Bateson, 1861~1926)等人确证了香豌豆的某些遗传因子始终连锁在一起,第二代性状分离的比例与孟德尔定律所要求的完全不相符合。这种反常情况使包括贝特森本人在内的孟德尔纲领的衷心拥护者们大为惊异。
三、摩尔根:从纲领的怀疑者到辩护士
后来对孟德尔研究纲领的进步和成功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摩尔根(T. H. Morgan,1866~1945),在刚开始时却对孟德尔纲领有过强烈的抵触情绪。在摩尔根心里有两大怀疑理由:1)发现显性/隐性假说及分离比例都存在反例。摩尔根曾以小鼠为材料做实验,旨在验证孟德尔定律,结果却发现融合遗传现象破坏了分离比例。[10]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显隐性关系可以发生转换,显隐性还可能同时呈现等现象。[11]第一个怀疑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显性/隐性这一辅助假说的。2)立足于胚胎学中的后成论(即渐成论)观点,力图否定或削弱细胞核和染色体在遗传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摩尔根是以胚胎学家身份开始其研究生涯的,因此他有很深的“胚胎学情结”。有关胚胎发育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预成论认为在精子、卵子中早就有了预先形成的微型新生物体,器官早就分化;后成论则认为,生物体中各个器官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在某种内在力驱动下逐渐成形的。当时后成论占上风。摩尔根对预成论的先验决定论十分反感,孟德尔纲领的“粒子遗传”观念因之受牵连。第二个怀疑的矛头,确实是指向孟德尔纲领的本体论预设的。
好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摩尔根和他的每一个得意门生正好都是出色的“实验主义者”。他们确信,一切理论分析都必须以实验数据为基础,理论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确证或证伪)。这也是科学哲学家的公认观点。摩尔根在《实验动物学》(1907)与《实验胚胎学》(1927)中都强调过,自己的假说有可证伪性,一旦被证伪,愿意立即就放弃。这也是爱因斯坦对待自己的物理学假说的批判性态度。摩尔根牢记马丁教授的教导,不要轻信“生理学灌肠机”,以为一头塞进动物,另一头就可以作出重大的科学发现。[12]科学哲学家也正是这样提醒大家:不要轻信归纳法万能论者的“归纳机器”,以为一端输进数据资料,另一端就能输出科学定律。摩尔根决不愿当盲目的操作机器,而是立足于可靠的事实,进行精细而有效的逻辑分析,大胆地且接二连三地提出新颖辅助假说,成功地消解一个个反常,从而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与进展。
1910年,摩尔根发现了果蝇白眼突变的伴性遗传现象,它成为摩尔根研究工作的理论突破口。伴性现象中所包含的关键性信息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使他对孟德尔纲领的理解产生了革命性转变。
在常规情况下,果蝇眼睛为棕红色,现在却在培养瓶中发现了一只奇特的白眼雄果蝇。这是果蝇实验室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反常事实。这只果蝇后来作为“明星动物”而载入遗传学史册。接着又发现伴性遗传的反常事实,如杂交子二代白眼果蝇全为雄性的。然而,按常规情况运用孟德尔原理来估算,子二代中应当有,隐性性状∶显性性状=白眼∶红眼=1∶3,并且与性别无关。换句话说,按常理在子二代中应当各有1/4雄果蝇和1/4雌果蝇是白眼的。可是,摩尔根在实验中实际观察到的却是,在子二代中雄果蝇有1/2为红眼的,1/2为白眼的;雌果蝇全部为红眼的,根本没有白眼的。总起来说,子二代白眼果蝇全部为雄性的。白眼果蝇在雌雄性别中分布不均衡的反常事实,看来是向孟德尔纲领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按照科学哲学的一般原理看,孟德尔的研究纲领不能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理论,它应当是由核心原理、辅助假说、先行条件等等组成的一个复合的整体。实验对理论的检验是整体论性质的。当出现反常情况,出现所推出的预言与事实不符时,受到反驳的不一定是核心原理,也可能是原先的辅助假说或先行条件在某一环节上出了问题。每一个纲领都是一个开放的科学假说集,它富有弹性与韧性,遇到反常,它可以灵活地修改先行条件、辅助假说、核心原理等任何一个环节,通过调整变形或添加新的辅助假说来适应新情况。一般说,不到迫不得已不会放弃核心原理。[13]这就是科学理论辩护的逻辑。摩尔根尽管对孟德尔纲领的真实性深表怀疑,但他同时持有正直科学家所应有的诚实公正的心态。摩尔根是熟悉孟德尔的推理思路的。他很想试试,若让孟德尔纲领的核心假说,结合巧妙而合乎情理的辅助假说,究竟能否战胜各种反常。他很想看看,孟德尔纲领的潜在启发力究竟有多大,推理究竟能走多远。他很想知道,孟德尔纲领究竟能否通过最严峻的检验,让那些看似不可信的预言梦想成真。如此真是这样,摩尔根随时可以放弃原有的错误立场。
摩尔根对染色体研究的新进展了如指掌。因为摩尔根的好友威尔逊(E. B. Wilson, 1856~1939)于1908年创立了性染色体学说。当时他俩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系任职,经常进行交流。按照性染色体学说,XX为雌性,而YY为雄性。若以孟德尔原理为核心假定,而以威尔逊学说为辅助假说,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假定白眼基因果真位于性染色体上,那末白眼雄性果蝇的基因型,就必须为X白Y白才行。因为只当双亲的基因型同为白眼隐性基因时,表现型才可能是白眼的。这是按常规推理说的。结果呢,反常情况仍然解释不通。
摩尔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教条地套用孟德尔纲领的常规解释,他敢于打破常规,大胆设想新的可能性。正如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所提倡的,要敢于引进与发明同似最可信的理论相违背的新假说(他称之为“理论增多原则”)。为此,摩尔根不仅成功地对“白眼雄蝇”这一反常事实作出了科学说明,而且推出了一系列可独立检验的新预言,特别是随后果真为新的实验一一确证。
若以“分离”与“自由组合”为孟德尔纲领的核心假说,则性染色体学说为其辅助假说。若从性染色体学说内部来看,则“XX为雌、XY为雄”是核心假说,而摩尔根的创新猜想“果蝇也许只有X染色体上带有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则为染色体学说的辅助假说了。整个说来,摩尔根对伴性遗传的猜想,是受了细胞学研究成果的启示(Y染色体作用较小),这在李思孟先生所著《摩尔根传》(1999)中有具体分析,[14]这里不再细述。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摩尔根借助于辅助假说是如何消解反常的,是如何开发孟德尔纲领的潜在启发力的。这是一个两步过程,一是解释,二是预测。首先,摩尔根利用孟德尔的硬核“分离”规律加上“唯X带有眼色基因”的辅助假说,合理地解释了自己的三个实验结果。
(1)野生红眼雌果蝇的一对X染色体上都带有红眼基因,记作X红X红;野生红眼雄果蝇则为X红Y,突变型白眼雄果蝇为X白Y。以白眼雄果蝇与野生红眼雌果蝇交配,其结果是(见表1):
野生 红眼雌蝇 × 白眼雄蝇
X红X红 X白Y
|
精子
杂 交
子一代 卵子 |
表1:白眼雄果蝇与野生红眼雌果蝇的杂交结果 X白 Y |
|
 X红 X红
|
X红X白 X红Y
(红眼雌蝇) (红眼雄蝇) |
可见,杂交子一代清一色地为红眼果蝇,雌雄各半。
(2)让子一代果蝇再进行自交,结果是(见表2):
子一代红雌 × 子一代红雄
X红X白 X红Y
|
精子
杂 交
子二代 卵子 |
表2:子一代红眼的雄蝇与
雌蝇的交配结果 X红 Y |
|
 X红 X红
X白 |
X红X红(红雌) X红Y(红雄)
X白X红(红雌) X白Y(白雄) |
可见,子二代的雌蝇均为红眼,而雄蝇有一半为红眼,另一半为白眼。反过来说,子二代的白眼果蝇都是雄的。
(3)让子一代的雌果蝇与白眼雄蝇回交,结果是(见表3):
子一代红雌 × 白雄
X红X白 X白Y
|
精子
回交
结果 卵子 |
表3:子一代红眼雌蝇与
白眼雄蝇交配结果 X白 Y |
|
 X红 X红
X白 |
X红X白(红雌) X红Y(红雄)
X白X白(白雌) X白Y(白雄) |
可见,将孟德尔核心假说与摩尔根辅助假说相结合,从理论上可以推出,白眼雌蝇、红眼雌蝇、白眼雄蝇与红眼雄蝇之比应当是1∶1∶1∶1。
这样摩尔根用白眼雄蝇实验所得到的全部已知观察结果,都通过引进新假说而在理论上得到完满解释。至此,第一步骤就完成了。然而,科学哲学家最忌讳的是“特设性假说”。它是为了应付反常而特别设计的,只能解释已知事实,却没有预言力。换句话说,它只能当“事后诸葛亮”,却推不出独立可检验的新预言。不过,摩尔根的假说决不是特设性的,因为它具有很强的预言力。接着,第二步骤是预测,摩尔根所设计的三个独立可检验的新实验(1)让子二代红眼雌蝇与白眼雄蝇交配;(2)让白眼雌蝇与红眼雄蝇交配;(3)让白眼雌蝇与白眼雄蝇交配。它们全都得到了预期效果,这里不再一一细述。[15]
摩尔根及其学派通过研究果蝇白眼突变的遗传发现了伴性遗传规律,从实验上把一个特定的基因定位于一个特定的染色体上,使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进一步研究,摩尔根发现并总结出基因连锁与互换的规律,史称遗传学“第三定律”。
摩尔根注意到,在果蝇实验中也存在贝特森所指出但未能作出正确解释的连锁现象。他发现果蝇的“黑身”与“残翅”是连锁的性状(1912)。
这种反常究竟应当看作危及孟德尔研究纲领的核心(遗传因子假说)的事实,还是只影响到萨顿的辅助假说(“不同因子必定座落在不同染色体上”)的事实呢?
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语言说,摩尔根经过深入思考后,使孟德尔纲领外围的“保护带变形”,通过修正辅助假说,“消化了反常”,从而维护了孟德尔纲领的“硬核”。具体地说,摩尔根对萨顿假说的修改是:并非一个基因占有整个染色体;许多基因可以排列在同一个染色体上。因此,不同基因既可以分布在不同染色体上(如孟德尔的豌豆七对性状的基因正巧是这样),也可以连锁在同一染色体上。这样孟德尔所要求的分离比例的“失调”就得到合理解释。
摩尔根的得力助手斯图蒂文特、布里奇斯(部分地还有缪勒)等人,个个都是假说演绎法的好手。他们不断从孟德尔纲领与染色体学说的核心思想中汲取启发力,不断面对新情况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假说,一次又一次地消解反常,并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及时得到确证的预言,使孟德尔纲领由胜利走向胜利,充分显示出该研究纲领的进步性。
第四节 摩尔根学派:科学共同体
科学哲学家T. S. 库恩指出,科学共同体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单位,它是指这样的科学家集团,他们从事给定的专业研究,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共同要素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彼此了解,思想交流充分,在专业上判断比较一致。同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拥护的共同纲领被库恩称作“范式”,它包括共同接受的世界观(对自然的总体看法)、价值观(评判好坏的标准)、所偏爱的科学方法与实验技术、样板理论及范例等等。摩尔根学派的共同纲领是孟德尔纲领(如前几节所详述)与萨顿假说的合理成分的整合,简要地说,其核心在于确信座落在染色体上的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它也可以称作染色体遗传学纲领。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特色性的东西,对摩尔根学派而言,是果蝇实验技术及高超的假设演绎法。
在科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既受内在的逻辑、方法论因素,又受外在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很大影响。在科学哲学中,逻辑主义派侧重于逻辑分析,而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派则更关注科学活动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心理学因素。这就使得科学哲学又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相互交叉。拉卡托斯有点特别,他把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人们常说“天赐良机”,如果说上天为孟德尔准备了豌豆,那末就可以说,上天又为摩尔根专门准备了果蝇,以便他们顺利地进行遗传学研究。除此之外,摩尔根还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学术环境中,那就是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以及一群可以帮他研究的得力助手。当果蝇被引进哥伦比亚大学用于研究时,E. B·威尔逊正是生物系主任。威尔逊是细胞学权威,德高望重。1896年初版的专著《发育与遗传中的细胞》是他的代表作,1908年他又创立了性染色体学说,他对进化与遗传也很感兴趣。威尔逊是发现摩尔根这个人才的“伯乐”,他将摩尔根调来,答应他少讲课多搞研究,竭尽全力让他安心做学问(摩尔根在那里工作长达24年)。有人说,没这位伯乐,也就没有摩尔根后来的果蝇研究。威尔逊曾在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得意地说过,他对遗传学的唯一贡献就是“发现摩尔根”。这被传为遗传学史中的佳话。[16]
细胞学与遗传学的联姻(两种研究纲领的整合),也与威尔逊与摩尔根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关。他们在同一幢大楼里工作,他们的办公室是近邻。1903年提出遗传因子与染色体的对应关系假说的萨顿,当时还是威尔逊的一名研究生。很自然,摩尔根对威尔逊及其学生的每一项细胞学研究成果了若指掌。摩尔根后来对果蝇的研究,成为遗传学与细胞学结合的典范以及染色体遗传的直接证明。之所以能这样,都与上述历史背景分不开。摩尔根与威尔逊堪称是“黄金搭档”。
说起“同一幢大楼”里工作的“黄金搭档”,使人联想起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来。1921年量子物理学家M. 玻恩是哥廷根大学物理系主任,他引进人才,把实验物理学“怪才”弗朗克调到身边来,从而实行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联姻,他们的工作室紧靠在一起,彼此间相互了解。弗朗克在实验室里天天都在做电子与光子的碰撞实验,因此“粒子性”在玻恩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26年波动力学派学者主张波就是一切,想要取消粒子的概念。玻恩坚决不答应,他用“统计阐释”协调了粒子与波之间的关系,最终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7]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成员间经常进行学术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启发,这是任何一种成功的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1909年和1910年,几个热情而聪敏的青年,来到果蝇实验室工作。他们是斯图蒂文特(A. H. Sturtevant,1891~1971),缪勒(H. J. Müller, 1890~1968)和稍后才来的布里奇斯(C. B. Bridges,1889~1938)。除缪勒已经是威尔逊的研究生外,其他两人当时还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摩尔根独具慧眼,不计学历只凭能力就选中了他们,不过后来都在摩尔根门下成为博士。摩尔根学派的这些精英和其他已经在果蝇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帮助确立了染色体遗传理论的主要原理。[18]
假如孟德尔式的因子在染色体上呈线性排列,那么就理应有某种方法来绘制染色体上因子相对位置的图。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染色体制图技术之由来。1909年詹森(F. A. Janssens, 1863~1924)提出“交叉假说”,认为两条同源染色体的某些对应片断可能发生了交换。摩尔根由此推想,这种物质交换导致基因重组,重组率高低反映出交换率的高低,两对基因相离越远交换率就越高。这一猜想发表在《孟德尔遗传中的随机分离结合》(1911年9月)。这一猜想尽管思辨性很强,却也很有启发力。摩尔根只是有了初步的想法,是斯图蒂文特使他梦想成真。斯图蒂文特后来说,摩尔根早已指出,基因连锁强度不同,与它们在染色体上的相对距离有关。这就使他在某一天,突然想到可以由此确定染色体上基因的排列顺序。于是在那天晚上他没有做作业,而是费了大半夜绘出了第一张基因连锁图。[19]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后几年内,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绘制染色体图的详细程序。1913年正式发表的染色体遗传学图,绘出了果蝇X染色体上六个基因的排列顺序。
摩尔根所领导的这个科学共同体比较团结,这些精英们都很有个性,个个都有自己的专门实验技巧和独特兴趣。摩尔根汇总并分析实验结果,并高瞻远瞩地指示新的方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大的难题。斯图蒂文特是摩尔根在1910年临时代课(讲动物学课)时认识的。斯氏家里开养马场,他对赛马的皮毛颜色及遗传问题有浓厚兴趣(可惜他患有弱色盲症),他的推理能力强,分析问题有条理、有深度,特别擅长于研究染色体图中的数学关系,经常成功地获得一些定量数据。这是令摩尔根最赏识的优点。他也是学生中最有口才,最敬佩摩尔根的人。布里奇斯是摩尔根学派中出色的细胞学家。他不仅具备高超的技能为染色体研究做一些细胞学准备,而且还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曾凭肉眼直接观察,透过厚厚的牛奶瓶壁发现了果蝇朱色眼突变,令摩尔根大为惊讶。他是发展染色体制图与实际染色体结构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
在摩尔根学生中,名声最大的是缪勒(他因研究X的射线诱发基因突变而得诺贝尔奖)。他的推理能力与想象力都很强,左右脑都发达,又擅长于设计精确而巧妙的杂交实验,用以检验自己或他人的假说。他与摩尔根之间的个人关系,不如其他二人那样亲密、和谐。也许缪勒作为最独立和最爱思考的人太有棱角了。总的说来,精英们取长补短,齐心协力,因此迅速取得了惊人成就与进步。
斯图蒂文特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科学共同体的:
这个小组工作起来像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实验,但是谁都确切地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而且大家自由讨论一个新的结果。大家都不太关注优先权或新思想、新解释的来源。大家关心的是如何推进工作。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新思想要检验,要发展许多新的实验技术。在众多的实验室中,没有多少实验室,能这么长时间地保持这种令人激动的氛围和热情。[20][21]
虽然在1910年后的几十年中,他们密切合作地发展了果蝇遗传学,但是无论布里奇斯还是斯图蒂文特,特别是缪勒,都不仅仅是摩尔根的助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卓有成就的研究者。
对摩尔根的果蝇小组,不少人存在一种误解。常有人曲解了这批“实验主义者”的信条:“一切都要经过实验”。在一般人眼里,实验家=具有灵巧双手的实验工匠,似乎进行复杂的推理只是理论家的职责,而思辨则是哲学家的特殊权利。可是,摩尔根的导师马丁教授关于“不要轻信生理学灌肠机”的话却启示我们,实验家的头脑比双手更重要。一个出色的实验家应当成为实验室里的思想家和推理大师。事实上,在摩尔根身边,人人都是假说演绎法的高手。
摩尔根是这个共同体的精神领袖,比他的学生与助手年长许多,但他为人谦和、没有架子,以平等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这些特点与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N·玻尔非常相似。整个摩尔根学派和果蝇实验室充满融洽与亲密无间的氛围。
我们曾在《海森伯与慕尼黑、哥廷根、哥本哈根三个科学共同体》[22]等文中分析过几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派各自的研究纲领、范式、方法论特征,精英人物各自的个性、风格与学术地位等等。整个说来,无论是生物学家集团还是物理学家集团的科学活动,都不违背科学哲学有关“科学共同体”的通用原理。
注释
[1] 参看海森伯:《原子论和对自然的认识》,载《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
社,1978年第134页。
[2] 参看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2.2原子论的自然观、§2.3毕达哥拉斯主义自然观,武汉大
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3页。
[3] 参看桂起权:《科学史上作为启发原则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载《科学探索的奥秘》,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161页。
[4] 参看赵功民:《遗传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5] 参看[德]H.斯多倍:《遗传学史》,赵寿元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6]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3页。
[7] 参看[美]T. 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
34页。
[8] 引自[美]N.玛格纳:《生命科学史》,李难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556页。
[9] [德]H·斯多倍:《遗传学史》赵寿元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10] 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11] 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2] 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3] 桂起权、任晓明:《科学辩护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载延安大学学报,2001(4)。
[14] 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15] 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16] 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7] 张德兴、桂起权:《哲人科学家:玻恩》,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18] 参看[美]E·艾伦:《20世纪生命科学史》,田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19] 参看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与79页。
[20] 引自[美]E·艾伦:《20世纪生命科学史》,田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1] 参看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21页。
[20] 引自[美]E·艾伦:《20世纪生命科学史》,田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1] 参看李思孟:《摩尔根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21页。
[22] 参看王自华、桂起权:《海森伯与慕尼黑、哥廷根、哥本哈根三个科学共同体》,载广州华南师大学报(社),2000(3)。
|